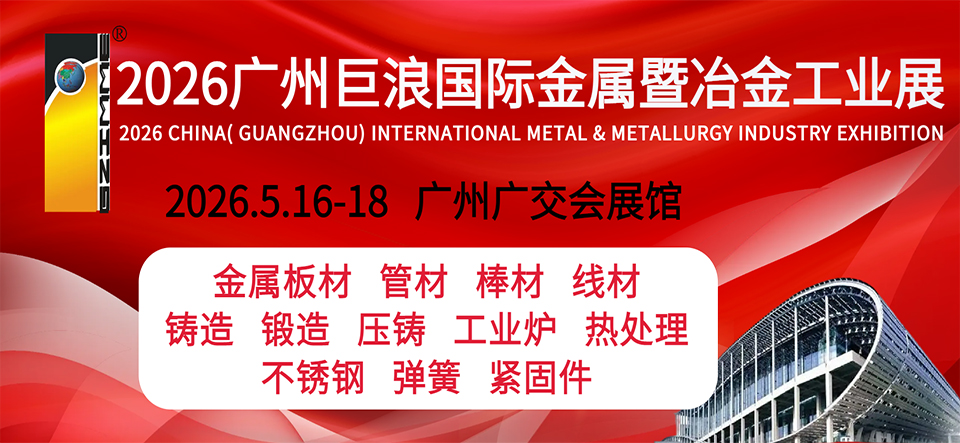月12日,北京,晴。
盡管湛藍的天空給人們帶來了愉悅的心情,但對于那些在京津冀小鋼廠工作的人來說,腦子里依舊繃著一根弦。反復“發作”的霧霾天氣,一次次地將鋼鐵產能過剩問題推向風口浪尖。
在舉國壯士斷腕般的治霾決心下,鋼鐵、水泥等排污大戶屢遭停產、限產,這使得原本就面臨“產能淘汰”的鋼鐵廠和數十萬職工雪上加霜。
淘汰帶來的陣痛
自“霾”這個詞出現以來,鋼鐵行業就一直因能耗高、污染大而廣受詬病。尤其是在京津冀地區,想解決產業結構偏重、能源結構單一、產能過剩等問題,鋼鐵首當其沖。
綠色和平與英國利茲大學課題組最新發布的《霧霾真相——京津冀地區PM2.5污染解析及減排策略研究》顯示:煤電、鋼鐵和水泥生產是京津冀首要“污染”行業,排放的煙塵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等是霧霾的主要來源。
因此,國務院在去年頒布的《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》中明確提出,2015年要再淘汰煉鐵、煉鋼各1500萬噸產能。這是繼去年國務院出臺《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》(以下簡稱《意見》)后,對鋼鐵業的又一重擊。
《意見》中明確要求,鋼鐵業在5年內削減8000萬噸產能,其中僅河北省唐山市就背負了一半的任務。
淘汰必然會帶來陣痛。
5年,4000萬噸,可能會換來一片藍天,但這個數字也意味著唐山市40多萬鋼鐵廠職工可能會“被下崗”。
“隨著各地逐步化解鋼鐵產能的嚴重過剩,如果社會托底工作做得不扎實,職工安置問題可能會引發社會穩定問題。”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院長李新創向《中國科學報》記者表示。
此外,鋼鐵產能的退出面臨著債務風險。據了解,當前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會員企業的負債率高達70%左右,貸款總額達1.3萬億元。加上非會員企業,全行業債務總額可能超過2萬億元。
“有些企業的建設項目使用了大量銀行貸款甚至是民間借貸,債務處置、合同糾紛等也是不可回避的。”李新創指出。
“狼”真的來了
為什么鋼鐵產能如此難“退”呢?
早在“十一五”期間,國家就開始探索建立鋼鐵產能退出機制。但鋼鐵產能仍舊“年年有余”,而且還“越余越多”。去年,中國鋼鐵產能過剩達2.8億噸,幾乎相當于歐盟產能的2倍。
同時,總部位于英國的鋼鐵工業和市場分析公司(MEPS)近日發布的報告顯示,2013年中國粗鋼產量與去年同比增長7.5%,已達7.79億噸,幾乎占據了全球粗鋼產量的半壁江山。
“如果十幾年前說‘鋼鐵產能過剩’就像喊‘狼來了’,那么這一次‘狼’真的來了。”在李新創的帶領下,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對中國鋼鐵產能的利用率、經營效益、產量等進行了系統分析。結果顯示,從2011年第四季度開始,中國鋼鐵產業已進入產能嚴重過剩期。
然而,為何鋼鐵產能仍然是“一座小高爐倒下去,新的大高爐又站了起來?”
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環境經濟學教授曾賢剛告訴《中國科學報》記者:“鋼鐵行業缺乏公平的淘汰機制,地方政府過度追求GDP考核制度,央企、國企則可以依靠財政補貼保存利益。”
而在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研究員黃順江看來,削減鋼鐵產能的問題在于“使用的方法不對,以行政命令手段進行產業結構調整、產能減壓難以達到好的效果”。
此外,鋼鐵產業本身具有資金密集、勞動力密集的屬性,也導致了轉產成本過高等問題。
建立完善的退出機制
猛藥去疴已成定局,到底如何化解淘汰帶來的陣痛?或許,鋼鐵產業也在等待各種政策的“春風”吹來。
曾賢剛認為,在建立鋼鐵產能退出機制中,核心問題是職工就業安置和企業轉型,要建立完善的企業退出援助機制。
黃順江則建議,鋼鐵產能的壓縮不僅要回歸市場本位、減少行政干預,而且要建立環保不達標的“一票否決制”。
為此,我國已開始研究新的落后淘汰標準,通過環保手段淘汰不達標的裝備設施、加大環保改造的投入和維護力度,倒逼企業提高環保成本。
李新創則提出,在建立鋼鐵企業動態管理制度的基礎上,完善市場調節機制,嚴格實施差別電價、懲罰性電價制度,加快推進環境保護費改稅,完善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,推進資源稅改革。
但化解產能過剩的矛盾也不能操之過急。李新創表示,要以長遠的綜合角度看待化解產能過剩的成效。尤其是霧霾等重污染天氣一出現,所有鋼鐵產能就都要按照比例停產、限產,很難促進落后產能的退出。
“目前來看,大多數地區的限產、停產政策是一刀切。”李新創指出,只有對于有落后產能的企業、環保不達標的企業實施限產、停產,才會促進落后產能的淘汰。
金屬展-冶金展-2014廣州巨浪國際金屬暨冶金工業展覽會-亞洲最大金屬冶金展-巨浪展覽-2014China(Guangzhou)Int’lMetal &Metallurgy Exhibition
|